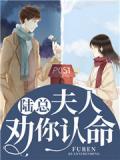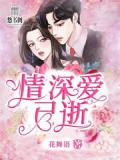精彩内容阅读
北宋之世,乃异军苍头特起。宋人之治经也,不墨守前人传注,而兼凭一己所主张之义理。其长处,在能廓清摧陷,一扫前人之障翳,而直凑单微。其短处,则妄以今人之意见,测度古人;据后世之情形,议论古事;遂至不合事实。自南宋理宗以后,程、朱之学大行。元延祐科举法,诸经皆采用宋人之书。明初因之。永乐时,又命胡广等修《四书五经大全》。悉取宋、元人成著,抄袭成书。自《大全》出,士不知有汉、唐人之学,并不复读宋、元人之书;而明代士子之空疏,遂于历代为最甚。盖一种学问之末流,恒不免于流荡而忘反。宋学虽未尝教人以空疏,然率其偏重义理之习而行之,其弊必至于此也。物穷则变,而清代之汉学又起。
清儒之讲汉学也,始之以参稽博考,择善而从,尚只可称为汉、宋兼采。其后知凭臆去取,虽极矜慎,终不免于有失,不如专重客观之为当也。于是屏宋而专宗汉,乃成纯粹之汉学。最后汉学之中,又分出宗尚今文一派,与前此崇信贾、马、许、郑者立别。盖清儒意主复古,剥蕉抽茧之势,非至于此不止也。
经学之历史,欲详陈之,数十万言不能尽。以上所云,不过因论读经之法,先提挈其纲领而已。今请进言读经之法。
治学之法,忌偏重主观。偏重主观者,一时似惬心贵当,而终不免于差缪。能注重客观则反是。今试设一譬:东门失火,西门闻之,甲、乙、丙、丁,言人人殊。择其最近于情理者信之,则偏重主观之法也。不以己意定其然否,但考其人孰为亲见,孰为传闻。同传闻也:孰亲闻诸失火之家,孰但得诸道路传述。以是定其言之信否。则注重客观之法也。用前法者,说每近情,而其究多误;用后法者,说或远理,而其究多真。累试不爽。大抵时代相近,则思想相同。故前人之言,即与后人同出揣度,亦恒较后人为确。况于师友传述,或出亲闻;遗物未煙,可资目验者乎。此读书之所以重“古据”也。宋人之经学,原亦有其所长;然凭臆相争,是非难定。自此入手,不免失之汗漫。故治经当从汉人之书入。此则治学之法如是,非有所偏好恶也。
治汉学者,于今古文家数,必须分清。汉人学问最重师法。各守专门,丝毫不容假借。如《公羊》宣十五年何《注》,述井田之制,与《汉书•食货志》略同。然《汉•志》用《周官》处,《解诂》即一语不采。凡古事传至今日者,率多东鳞西爪之谈。掇拾丛残,往往苦其乱丝无绪;然苟能深知其学术派别,殆无不可整理之成两组者。夫能整理之成两组,则纷然淆乱之说,不啻皆有线索可寻。
今试举一实例。如三皇五帝,向来异说纷如,苟以此法驭之,即可分为今古文两说。三皇之说:以为天皇十二头,地皇十一头,立各一万八千岁;人皇九头,分长九州者,《河图》《三五历》也。以为燧人、伏羲、神农者,《尚书大传》也。以为伏羲、神农、燧人,或曰伏羲、神农、祝融者,《白虎通》也。以为伏羲、女娲、神农者,郑玄也。以为天皇、地皇、泰皇者,始皇议帝号时秦博士之说也。除《纬书》荒怪,别为一说外,《尚书大传》为今文说,郑玄偏重古文。伏生者,秦博士之一。《大传》云:“燧人以火纪,阳尊,故托燧皇于天;伏羲以人事纪,故托羲皇于人;神农悉地力,种谷蔬,故托农皇于地。”可见儒家所谓三皇者,义实取于天地人。《大传》与秦博士之说,即一说也。《河图》《三五历》之说,司马贞《补三皇本纪》列为或说;其正说则从郑玄。《补三皇本纪》述女娲氏事云:“诸侯有共工氏,与祝融氏战,不胜,而怒。乃头触不周之山,天柱折,地维缺。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”云云。上言祝融,下言女娲,即祝融即女娲。《白虎通》正说从今文,以古文备或说;或古文说为后人窜入也。五帝之说,《史记》《世本》《大戴礼》并以黄帝、颛顼、帝喾、尧、舜当之;郑玄说多一少昊。今案《后汉书•贾逵传》。逵言:“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,而尧不得为火德。《左氏》以为少昊代黄帝,即图谶所谓帝宣也。如令尧不得为火德,则汉不得为赤。”则《左氏》家增入一少昊,以六人为五帝之情可见矣。《史记》《世本》《大戴礼》,皆今文说,《左氏》古文说也。且有时一说也,主张之者只一^人;又一•说也,主张之者乃有多人。似乎证多而强矣。然苟能知其派别,即可知其辗转祖述,仍出一师。不过一造之说,传者较多;一造之说,传者较少耳。凡此等处,亦必能分清家数,乃不至于听荧也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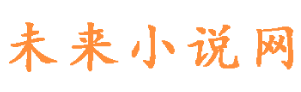
 书库
书库